《范公堤》[范公堤] - 第七章 道義之樂(2)
仲淹的眉頭越皺越緊,晏殊素有「簡約」之名,尚且如此奢侈,其他達官權貴可想而知!最糟糕的是,世人不以為錯,反而羨慕、讚美,恨不能參與其中!前面說過,大宋吸取前朝特別是大唐盛衰興亡的歷史教訓,為杜絕宦官、宗室、后妃、外戚和武人擅權之禍,做出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」的抉擇,將士大夫群體作為唯一信賴依託的對象。自宋太祖以來,重文輕武成為祖宗家法,科舉制度的改革使得官僚集團的主體部分都是來自科舉考試。應該說,歷史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正確,不同於前面的歷朝歷代,大宋整個一朝,皇帝的地位非常穩固,所謂「看不見篡奪」。整個宋朝,從來沒有皇帝被摒棄,其他政治勢力成為國家主導力量的政變,最後的滅亡是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外族入侵顛覆。支撐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以宰相為代表的士大夫勢力,宋代宰相自稱「措大」即一介窮書生,所有文人掌管着大大小小的權力,而都心甘情願地臣服於天子。宋太宗對宰相李昉等說「天下廣大,卿等與朕共理,當各竭公忠,以副任用」,在這種定論之下,大宋的大臣俸祿豐厚,收入名目繁多:正俸(俸錢,衣賜,祿粟),加俸(職錢,衣糧,茶酒廚料,薪蒿碳鹽,各種添支及爵勛供給),「恩逮其百官唯恐其不足」,可以說「重文輕武」已經演化為「以文能貴」。問題是,文人顯達的目的是什麼?就是為了奢侈生活,吃喝玩樂「又雅又有趣兒」嗎?糟糕的是,不是一人兩人一個馮縣令,而是莘莘學子和大小官吏普遍這樣想。范仲淹的兩道濃眉皺成了山峰。前天,晏洛望邀去看蔡慎留下來的鹽倉監官舍,在西溪東南角向陽的位置,好一幢齊整的府邸!亭台樓閣雕樑畫棟,曲廊迂迴中俯身觀魚,飛檐翹角旁遠眺大海,是舒適愜意,是心曠神怡,可西溪荒隅連遇天災,海潮肆虐民不聊生,怎忍在這豪宅中獨自享樂?晏洛望勸了范仲淹幾句,直到聽見他「人苟有道義之樂,形骸可外,況居室乎!」的激憤之語才住口,晏洛望鋒芒畢露的面容上有幾分沉思。這些道理,居然是他第一次聽到!唉,三槐堂有什麼不好?即使母親來,也夠住了。晏洛望察覺到范仲淹的不快,笑着轉換話題,說起了捍海堰。馮縣令瞥了眼范仲淹,轉身面向晏洛望很誠懇地回答:這麼大的事,他一個偏遠之地興化縣的縣令,能做什麼?倘若貿然上書建議,最好的結果是沒人聽,壞的結果很可能挨頓罵,再壞的結果不可預料!你們想過沒,為什麼前面這麼多任看着海潮侵害不吭聲?捍海堰能擋住海潮,可也能導致內澇!唐朝「常豐堰」修起後發生過,連天秋雨後因泄洪不暢導致積澇,淹沒大片良田鹽場,死傷百姓無數!這一個修建捍海堰的建議,焉能貿然提出?考證過利弊嗎?有詳細計劃嗎?切實可行嗎?做官做事,不能只憑一腔熱情,一時興起,如果思慮不周,是要釀成大禍的!范仲淹急得立起身,熱切地說:「這些下官都在做!只要大人首肯,向朝廷申告建議!」馮縣令擺擺手,放輕了聲音說:「本官還有一年即逢磨勘,如無例外將升遷回中原。這個時候,實不欲節外生枝。兩位見諒。」說是「兩位」,眼睛只望着晏洛望。晏洛望連連稱是,祝馮縣令磨勘順利,並表態如馮縣令但有需他向晏殊大人開口的儘管吩咐,拉着范仲淹告辭出了興化縣衙。出人意料,晏洛望一路沉默什麼都沒說,范仲淹忍不住憤然道:「磨勘磨勘,坐等陞官!三年任滿等升遷,但求無功無過,不顧國計民生!」大宋的官員升遷是磨勘制,文官三年一遷,武官五年一遷,不問好壞基本都一樣,所謂「坐至卿監丞郎」。這麼簡單易行的仕途之路,身為大宋官員,且是科舉進士及第出身的官員,范仲淹不應該慶幸嗎?晏洛望再一次奇怪地望着上司,說:「下官明白大人憂國憂民之心。不過捍海堰非同小可,恐怕非吾等力所能及。」范仲淹不再多說,獨自悶悶地轉回了下處。「范大人可回來了!您這腿難不成是不想要了?」一個童顏鶴髮銀須飄飄的老者笑着迎了出來,嗔怪的話語中滿懷關心。是大夫林逋,近古稀的年紀,身體卻頗硬朗,從他所住的西湖嶺步行至西溪要有十來里路,他卻堅持自己步行來回不肯讓衙門車馬接送,據他說健步走小半個時辰也就到了,令范仲淹自嘆不如。林逋談吐頗不凡,知識又極淵博,療傷之時天南海北地聊,常有驚人之語。范仲淹猜他是個有來歷的,他卻笑笑「老嘍,行醫治病而已,過去的都忘記嘍」,並不肯多說。老人唯一的愛好就是美食,有次恰逢董二家的來探望范仲淹,帶了盆「一鍋鮮」,逢春擱在紅泥爐上小火煨燉,香飄滿屋,林逋開始還客氣推辭,喝了一小盅湯後便毫不猶豫地換了大碗,直喝盡了三大碗撐得肚滾腰圓才作罷。銀針翻飛,要扎一炷香工夫,逢春沏了壺碧螺春,連同一碟薺菜春卷,一碗煮乾絲端上來。林逋大喜,夾了根春卷就嚼,逢春抿嘴笑:「林大夫慢點,才出鍋,燙呢!」果然林逋燙得嘴巴大張,又不捨得吐出來,翻着白眼左右倒騰,奮戰了好半天才瞪眼伸脖地咽下去,忙不迭又夾了一筷,一邊誇獎:「范大人,你這小廝真不錯,烹調手藝沒得話說!你這以後有口福了!」「林大夫不嫌棄,儘管常來一起享口福就是。」范仲淹笑說。「不行。」林逋搖了搖頭,「我聽說了你范家的家規,沒客人的話就一個葷菜。要是為了我總破規矩,老夫可當不起。」「家規乃家母所立,是戒奢惜福之意,」范仲淹笑道,「可不是閉門謝客。」「哦?老夫人高壽了?現在哪裡,范大人的職田嗎?」林逋嚼着春卷,滋味無窮地問。大宋官吏的俸祿中含有職田,「以官莊及遠年逃亡田充,悉免租稅,佃戶以浮客充」,一般都賜封在官吏的祖籍處。范仲淹自長山朱家憤而出走的時候就決意自立門戶,可算能夠實現了,職田想來想去最後選在了應天府寧陵縣(今河南商丘市寧陵縣)。應天府好理解,距離汴京不遠,是讀書多年的地方,為什麼在寧陵呢,也很簡單,應天府轄六縣:寧陵,楚丘,虞城,下邑,谷熟和宋城,范仲淹當時只是個九品小官,楚丘等熱門縣都是高官要職聚集之地根本沒田,而寧陵因相對僻遠,閑田較多。「所以老夫人現在在寧陵?」林逋有些詫異,「老人家一個人嗎?」「在寧陵。我的兄弟,」范仲淹講到這裡有些遲疑,「朱諾和朱謙在侍奉她老人家。」林逋更加不解,不過體貼地低頭猛吃不再多問。范仲淹倒過意不去,解釋道:「家母是再適長山朱氏的。所以,所以這兩個兄弟姓朱……」「哎,管他姓朱還是姓范,都是你兄弟!古語說得好,打死不離親兄弟吶!」林逋放下手中碗筷,認真說,「范老爺大才,自然知道唐朝的姚崇大人。只要有經天緯地之才,一點點家事算得什麼。」姚崇是唐代武則天、睿宗、玄宗三朝宰相,為開元盛世第一功臣。他祖籍河南陝縣,父親去世後母親改嫁黃姓人家,這些范仲淹當然知道,不過聽林逋這麼說,倒觸動了他另一樁心事。姚崇曾問母親百年之後是否與父親合葬,其母答曰:「人若有靈,縱隔千里也相知;人若無靈,即便埋在一起也枉然。」所以最後姚崇將母親安葬在了萬安山下。林逋是拿姚崇來安慰自己,不過雖然如今母子團聚,可是以後呢?將來母親百年終老,該安葬何處?現在自己總算姓回了「范」,與族人,與三兄范仲溫相處都算融洽,可是母親已經改嫁朱氏,再不可能回范家。可如果葬入朱家祖塋,那難道以後自己都不能陪她?母親這一生坎坷流離,她體諒兒子從不提這事,然而早晚都是要面對的。茶香裹着春卷香,裊裊升騰。范仲淹皺了皺眉,心事重重。
-
連載中116 章

沈月卿裴知衡
好像從10歲開始,她就一直一個人一個人吃飯,一個人練劍,一個人上戰場她的父母,兄長,到現在的裴知衡,都在被蕭涼兒一點點搶走他們都偏愛那個裝羸弱的蕭涼兒,似乎已經沒人在乎她好不好,受不受傷......
-
連載中116 章

蘇清清賀明硯txt
《蘇清清賀明硯txt》小說是蘇清清傾心創作的一本穿越言情類型的小說,主角是賀明硯蘇清清,情節引人入勝,非常推薦主要講的是:排骨清洗好後冷水下鍋,加入料酒,薑片,煮出浮沫撈出,放入高壓鍋,加入切成大塊...
-
連載中116 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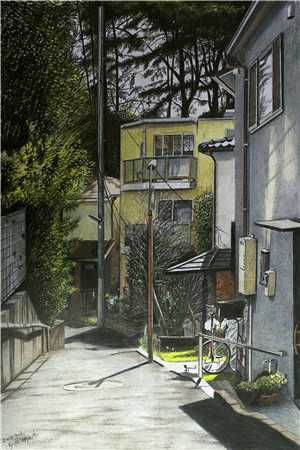
桑瓔陸徎
桑瓔跟何穗的關係一般,從陸徎第一次帶桑瓔回陸家的時候,何穗就看不上桑瓔陸徎一直不喜歡桑瓔和陸家聯繫太密切,除非必要,通常不會讓她去陸家桑瓔又撥了個電話過去這次接電話的倒是陸徎,他喉嚨里蘊了些笑意...
-
連載中116 章

付胭霍銘征
付胭心跳一緊,霍銘征又要發什麼瘋!毫不遲疑用力握着門把往回拉,不料霍銘征另一隻手直接攥住她的下巴,她只覺眼前一黑,鋪天蓋地的吻瘋狂地碾壓而來「你放開……」付胭咬緊牙關不鬆開,從齒縫溢出抗拒...《...
-
連載中116 章

隋兵霸途岳嘯天劉巧巧
名字是《隋兵霸途岳嘯天劉巧巧》的小說是作家鵝地山人的作品,講述主角岳嘯天劉巧巧的精彩故事,小說內容章節生動充實,故事情節曲折動人,推薦各位讀者大大閱讀!下面是這本小說的簡介:...《隋兵霸途岳嘯天劉巧...
-
連載中116 章

裴衍沈雲煙
她聽見裴衍滿含怒氣的聲音從上方傳來「沈雲煙,你現在真的骯髒不堪」...《沈雲煙裴衍全文閱讀》第5章免費試讀沈雲煙的腦子『轟』的一聲炸了此刻,她已經全然沒了一個做為人的尊嚴她羞愧得閉上眼,一滴狼...


 上一章
上一章 下一章
下一章 目錄
目錄